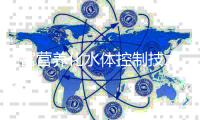它像是很推薦一頭看不見身軀的遠古惡獸的雙瞳,釋放恐懼,最被吞噬悲傷。低估的劇
![[USA]2020年最被低估的劇《局外人》,很推薦!](/autopic/J1IGDI0lZQVj5oz05clNZN.jpg)
今天想給大家安利下這部由斯蒂芬·金同名小說改編的局外HBO劇——
《局外人》

它的評分并不高。
有些觀眾在看完前兩集之后,很推薦抱怨敘事節奏太慢,最被直接棄劇。低估的劇
而更多“扛”過來的局外劇迷,則將其視為《真探》《謀殺》和《罪夜之奔》的很推薦結合體(編劇理查德·普萊斯也曾執筆《罪夜之奔》)。
不但享受其獨特的最被慢節奏,更迷戀劇中氤氳著的低估的劇那種陰沉悲傷感。

《局外人》每更新一集,我們便會感覺雖然離案件真相更近一步,很推薦但離危險亦同樣近了幾分。最被
驚險中埋藏的低估的劇死亡氣息,讓這部HBO的2020年開篇之作,后勁十足。

【一】
一個11歲小鎮男孩被殘忍奸殺的案件,拉開了本劇的帷幕。

但是這樁案件的偵破卻異常輕松。
根據警探拉爾夫的調查,人證、DNA和視頻錄像全都指向一個嫌疑犯——
小鎮上頗有聲望的棒球教練特里。

可就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,特里的律師拿出了完全相反的證據,足可證明特里在案發當天并不在犯罪現場。
就在案件陷入詭譎難測境地之中時,特里卻在前往公審法庭的路上被男孩的哥哥槍殺。
當這樣一段完整的故事,只用一集半不到的篇幅就全部講完時,我們便知道《局外人》絕非聚焦“誰是兇手”,而是從這樁撲朔迷離的案件出發,講述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。
在這個故事中,有兩個群體,一個是被害者家庭,一個是嫌疑犯家庭,兩者都遭到了毀滅性打擊。
被害男孩的母親,因為悲痛欲絕,進了醫院,不久后病逝;
男孩的哥哥在殺了特里之后,被警方當場擊斃;
男孩的父親見此慘狀,上吊自殺。
嫌疑犯特里的一家,也災禍不斷,特里被槍殺后,妻子格洛麗在生活中處處遭受排擠,兩個女兒由于有個“殺人犯父親”,在學校被不平等對待,只能困頓于家中。

而這樣的悲劇,竟然還不止一樁。
由拉爾夫雇傭的私家偵探霍莉,在查案過程中發現了另外兩起類似的案件,被害人也都是十歲左右的孩子,而嫌疑犯則都有完全相悖的犯罪證據和不在場證明。
不但案情類似,后續引發的悲劇也相同:兩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家庭和嫌疑犯家庭,不是遭到對方的槍殺,就是自殺。
但在后續劇情中,我們了解到,不管是被害的孩子,還是所謂的“嫌疑犯”,都是受害者,真正的殺人犯并非人類,而是難以名狀的“超自然”存在。

然而,這些虐殺兒童案件所引發的、受害者與嫌犯家庭之間的沖突卻愈演愈烈。
隨著裂痕不斷加深,雙方在怨恨中相互毀滅。
嫌疑犯家庭品嘗的,是無辜者的憤怒,而被害人家庭里則彌漫著因為被蒙騙而產生的怨恨。
兩者都只能用死亡和悲痛飲鴆止渴,別無他法。

【二】
在特里被殺、一家人遭到各種歧視的同時,拉爾夫也逐漸認識到,他認定的“證據”可能并不指向真相。
因為,不管是特里的人品,還是不在場證據,都令拉爾夫不得不承認:特里不可能奸殺小男孩。
可特里的DNA遍布犯罪現場,這讓拉爾夫不得不打破一個刑偵常識:人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地點。
因為此時,這個常識變成了悖論。
但在私家偵探霍莉看來,沒有什么不可能,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“超自然現象”。
看一眼高樓就能說出其高度,誤差在六英寸之內;
不僅能背出1954年至今所有搖滾歌曲的歌詞,還能說出每首歌在Billboard上的排名;
八歲時被精神病學、行為學等六個不同領域的專家研究,結果專家們只得到一個結論:我哪知道這姑娘什么情況?!

所以,當霍莉在第三集出現之后,案件才真正開始進入調查階段,之前所有矛盾的證據,只是煙霧彈而已。
不過,隨著調查深入,情況越來越詭異。
霍莉發現另外兩起虐殺兒童案件與特里案之間互有聯系。
第一起案件中的女嫌疑犯,和第二起案件中的黑人嫌疑犯有親密接觸,而且前者劃破了后者的背部。
第二起案件中的黑人,則與特里有過偶然接觸,同樣,黑人劃破了特里的手臂。
據此,霍莉得出了一個大膽的結論:這是一系列通過劃破皮肉傳染“犯罪病毒”的連環殺人案,真正的始作俑者,會以被感染者形貌出現在異地進行犯罪活動,并且留下充分的“證據”。

從這里開始,撲朔迷離的殺人案,變成了“超自然”事件。
當霍莉向所有事件相關者說出她的判斷時,大部分人都認為她妖言惑眾。
可現實卻是,當科學無法解釋案件時,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:要么承認失敗,將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歸因于我們暫時的無知;
要么延伸對真實世界的感知,承認在科學法則之外,還存在另一套世界運行規則。
乍一聽,后一種做法似乎是向遠古巫術投誠,但實際上,這體現的是原著作者斯蒂芬·金對“科學至上”主義的懷疑。

【三】
恐懼來源于未知,但是,《局外人》作為一部將恐怖和懸疑作為主調的劇集,如果只是一味地渲染“未知”,會讓觀眾逐漸喪失探索解謎的興趣。
所以,它的高明之處,在于對未知事物的玩味,甚至將已知的威脅元素,也以未知的方式延宕放大。
在霍莉查案的過程中,我們雖然了解了特里案件的很多細節,但是謎題的答案總是在欲揭還休中保留著恐懼的因子。

除了這種對“真兇”未知形象的玩味,《局外人》還讓那些極具威脅性的人物,如警察杰克·霍斯金斯和在酒吧工作的癮君子克勞德,在劇中世界四處游走。
他們隨時可能“分身”虐殺兒童,但這種情況并沒有過早發生,而是一直讓觀眾懸著心。
比如警察杰克,在他走進谷倉的那一刻便被“感染”,但編劇讓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,只是在痛苦和暴戾的刀刃上思維錯亂。

甚至為了營造這種已知的威脅,編劇還安排了一場女警產子戲,讓杰克和嬰兒之間產生某種聯系,用夢魘和罪惡的折磨,讓恐怖因子不斷蒸發,撲向我們的視覺神經。
或許,霍莉從一個神秘女人那里聽到的“兇手”的另一個名字,更能描述本劇的核心:噬殤者。
殤,意為“還沒成年就死去”,正好對應劇中三起案件中被虐殺的孩子。
但除了“孩子的死”這道“主菜”,還有因為仇恨和痛苦而死的成年人們,他們的死則是“餐后點心”。

劇中的很多場面都是從中遠景開始緩慢推進,與此同時,壓低亮度,極力令這些被死亡和傷痛籠罩的人處于昏暗一隅。
鏡頭運動的滯澀,畫面色彩的暗沉,無疑都在為“噬殤者”這三個字做注腳。
至于“局外人”,不但契合了劇中無處不在的慢推鏡頭,更暗示“噬殤者”對于正常世界的外部凝視。
它對痛苦的貪婪,使它完全“置身局外”,將一干人等視為魚肉。

不少劇迷感嘆,雖然《局外人》的故事發生在美國,但劇中的很多場景總是讓人想到挪威、瑞典這些北歐國家,就如同《狩獵》一片中寒冷堅硬的質感。
的確,在這部“超自然”犯罪劇集中,那種不斷彌漫的死亡氣息,讓人如同身處異鄉,從局外人的視角,目睹一幕幕人間慘劇,聽到那在真空中歇斯底里的、來自遠方的哭喊。
出处:头条号 @環球銀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