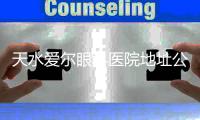今年2月28日,波灣是戰(zhàn)爭(zhēng)週年作戰(zhàn)以美國(guó)為首的多國(guó)部隊(duì)擊敗海珊(Saddam Hussein),取得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勝利30周年的沙漠紀(jì)念日。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的風(fēng)暴勝利,不只幫美國(guó)一掃越戰(zhàn)失利的空中陰霾,還為21世紀(jì)的成功從空戰(zhàn)模式拉開序幕。從1991年1月17日「沙漠風(fēng)暴」(Operation Desert Storm)發(fā)起開始,讓空到2月28日雙方結(jié)束交戰(zhàn)為止,權(quán)無長(zhǎng)達(dá)43天的用論戰(zhàn)鬥中,地面部隊(duì)只參與了四天共100小時(shí)的消失戰(zhàn)鬥而已。

換言之,波灣這場(chǎng)戰(zhàn)爭(zhēng)基本上可以說算是戰(zhàn)爭(zhēng)週年作戰(zhàn)靠空中武力打贏的,尤其是沙漠來自美國(guó)的空中武力。打從1903年飛機(jī)誕生以來,風(fēng)暴美國(guó)就是空中靠著空權(quán)力量登上世界第一強(qiáng)權(quán)寶座的。相信對(duì)於這一點(diǎn),無論各位讀者是喜歡還是討厭美國(guó),都不會(huì)有太多的疑問。然而空權(quán)在美國(guó)的發(fā)展,其實(shí)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順利,這能解釋為什麼美國(guó)空軍要等到1947年才脫離陸軍獨(dú)立的原因。
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空戰(zhàn)英雄,有「美國(guó)空軍之父」外號(hào)的米契爾(William Mitchell)少將,更因?yàn)樘岢鲎尶哲姫?dú)立於陸海軍體系之外的主張,得罪了美軍裡的保守派,最後落得被送上軍事法庭,提早於1925年退役的下場(chǎng)。航空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期間的大放異彩,並沒有讓「空權(quán)無用論」的聲音被徹底壓制下去。
美國(guó)對(duì)日本與德國(guó)實(shí)施的無差別轟炸,給無數(shù)平民帶來了「附帶損害」(collateral damage),卻沒有如米契爾將軍所預(yù)料般的摧毀德日兩國(guó)抵抗意志。儘管日本的投降,確實(shí)可以歸因B-29轟炸機(jī)投下的原子彈,可許多戰(zhàn)略家認(rèn)為那是「核子戰(zhàn)略」取得的作用,而不能算是「空權(quán)戰(zhàn)略」取得的作用。戰(zhàn)略轟炸與原子彈造成的人道危機(jī),更是讓美國(guó)空軍打從誕生以來就飽受輿論批判。
尤其是接下來的韓戰(zhàn)與越戰(zhàn)中,美國(guó)空軍發(fā)起的空中打擊仍持續(xù)造成無辜平民死亡,可實(shí)際上給敵人造成的損害卻相當(dāng)有限。美軍在越戰(zhàn)期間投下750噸炸彈,為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時(shí)投下的炸彈總噸量的兩倍,可最後卻仍然無法達(dá)成阻止北越武力併吞南越的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。所以空權(quán)理論的發(fā)展,在越戰(zhàn)結(jié)束後一度陷入瓶頸之中。
所幸在1986年10月4日,雷根(Ronald Reagan)總統(tǒng)簽署了由高華德(Barry M. Goldwater)與尼可拉斯(William F. Nichols)兩位跨黨派參議員推動(dòng)《高尼法案》(Goldwater–Nichols Act),加快了美國(guó)軍事事務(wù)革命(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)的腳步。全新的空中作戰(zhàn)理念,經(jīng)由此一軍事事務(wù)革命被引入了美國(guó)空軍,為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的勝利打下基礎(chǔ)。
 Photo Credit: AP / 達(dá)志影像
Photo Credit: AP / 達(dá)志影像五環(huán)理論(Five Rings)
提到「沙漠風(fēng)暴」行動(dòng)的頭號(hào)功臣,當(dāng)屬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空戰(zhàn)計(jì)劃主持人約翰?沃登三世(John Warden III)上校,還有他所提出的「五環(huán)理論」。嚴(yán)格來講,雷射或衛(wèi)星導(dǎo)引炸彈等智慧型武器,其實(shí)在越戰(zhàn)時(shí)代就已經(jīng)問世,並為美國(guó)空軍投入於對(duì)北越橋樑的空襲行動(dòng)之中。要等到越戰(zhàn)失敗後,經(jīng)由沃登將軍「五環(huán)理論」的提出,精靈炸彈才成為改變整個(gè)戰(zhàn)局的武器。
沃登將軍的「五環(huán)理論」之中心點(diǎn),為一個(gè)國(guó)家領(lǐng)導(dǎo)階層(Leadership),然後向外依序擴(kuò)張為有機(jī)要素(Organic Essentials)、基礎(chǔ)設(shè)施(Infrastructure)、人民(Population)與野戰(zhàn)部隊(duì)(Field Forces)。對(duì)於沃登將軍而言,過去那種動(dòng)輒出動(dòng)上百架轟炸機(jī),對(duì)目標(biāo)投下上千噸炸彈的無差別轟炸實(shí)在是浪費(fèi)資源,還將讓美國(guó)處?kù)断喈?dāng)不利的道德地位。
所以針對(duì)平民的無差別轟炸,不再為沃登將軍所鼓勵(lì),取而代之的是以精準(zhǔn)導(dǎo)引炸彈快速殲滅敵人的領(lǐng)導(dǎo)階層和野戰(zhàn)部隊(duì),以最有效率的方法在短時(shí)間內(nèi)結(jié)束戰(zhàn)爭(zhēng)。以此原則為基礎(chǔ),就有了德普拉圖(David A. Deptula)將軍提出的「效能作戰(zhàn)」(Effects-based Operations),即以達(dá)成軍事還有政治效果為導(dǎo)向的作戰(zhàn)模式,而非如同越戰(zhàn)以前那般純粹以殲滅敵國(guó)軍民為目標(biāo)。
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的成功,首先反映在多國(guó)聯(lián)軍還有美國(guó)海陸空三軍之間緊密的配合上,這有賴於參謀首長(zhǎng)聯(lián)席會(huì)主席鮑爾(Colin L. Powell),還有中央司令部司令史瓦茲柯夫(Norman Schwarzkopf)兩位陸軍將軍傑出的指揮能力。而美國(guó)海陸空三軍的協(xié)同作戰(zhàn)能如此成功,則又要?dú)w功於《高尼法案》的通過,大幅度精簡(jiǎn)了原本美軍複雜的指揮體系。
可見新科技與新技術(shù)的誕生,並不是真正改變戰(zhàn)局的決定性因素。美軍能在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中贏得漂亮,除了老布希(George H. W. Bush)團(tuán)隊(duì)卓越的外交與政治手段外,最重要的還是主事們願(yuàn)意接受新科技與新技術(shù),而且把這些新科技與新技術(shù)用在對(duì)的地方。正確的政治目標(biāo)搭配準(zhǔn)備充足的軍事手段,美軍打從一開始就注定成為這場(chǎng)「沙漠風(fēng)暴」行動(dòng)的勝利者了。
 Photo Credit: AP / 達(dá)志影像
Photo Credit: AP / 達(dá)志影像對(duì)戰(zhàn)場(chǎng)環(huán)境的全面掌握
波灣戰(zhàn)爭(zhēng)的空中作戰(zhàn),與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、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、韓戰(zhàn)還有越戰(zhàn)的最大不同之處,是美國(guó)空軍、海軍以及陸戰(zhàn)隊(duì)的飛行員都不再有「騎士精神」。他們?cè)陂L(zhǎng)官的要求下,不再執(zhí)著於與伊拉克空軍打公平的空對(duì)空作戰(zhàn),而是精確的情報(bào)導(dǎo)引下,將伊拉克空軍的各型戰(zhàn)機(jī)直接摧毀於地面上。換言之,伊拉克空軍連起飛還擊的機(jī)會(huì)都不會(huì)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