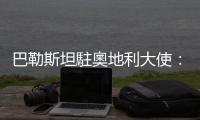疾病周期研究,疾病疾險很有的周期做。比如:傳染病、研究醫(yī)療用段慢性病、管理精神心理疾病、險重重大疾病、品共罕見病在疾病發(fā)生周期、疾病疾險疾病管理周期上,周期都有明顯區(qū)別。研究醫(yī)療用段這五個類別的管理疾病在保險共付水平、醫(yī)保支付方式上,險重彼此也有很大差距。品共

疾病周期研究,疾病疾險傾向于疾病自然進展,周期是研究醫(yī)療用段消極的。疾病周期管理,傾向于疾病人為干預,是積極的。以腫瘤疾病為例,前者關注分型、分期;后者關注治療方案的可及、療效、經(jīng)濟。結(jié)合兩者,保險才算懂得治療。
醫(yī)療險、重疾險對疾病周期研究、管理的能力積累均十分孱弱,目前有兩條道路進取:一是患者端,從群體到個體,研究有代表性的需求和風險保障;二是從醫(yī)療端,從個體到群體,找到可以復制的生態(tài)合作閉環(huán)。
關于患者、醫(yī)院反饋的治療數(shù)據(jù)(疾病細節(jié)、費用結(jié)構(gòu))不足、有限問題。筆者認為:及早推行“一人一碼”的健康檔案是重要的。這使保險公司把配合疾病管理服務做基礎,把設計健康保險產(chǎn)品做可靠創(chuàng)新陣地。
一方面,把真實發(fā)生數(shù)據(jù)作為首要教材,弄清楚極端只為一人提供專項或若干項健康保障時,合理費用區(qū)間、費用災難程度、風險可保性質(zhì);另一方面,把弄清楚的案例,從全要素向外拓展,聚類精算,并框定產(chǎn)品。
重疾險從未如此深刻地關注治療,或者說,重疾險在醫(yī)療險崛起的時期,也在享受醫(yī)療、保險效率互動的紅利。重疾險的風險保障范圍客觀上在縮小,醫(yī)療險的風險保障范圍卻在不斷擴延,兩者都是被迫如此演變。
于是,有一種潛在的逆反趨勢:重疾險在一些有特色的病種上逆勢擴張,同時關注控費、資金效益;醫(yī)療險在一些有特色的病種上被迫覆蓋,同時關注控費、資金效益。疾病管理、健康管理是這類病種的合規(guī)標簽。
比如:這一些病種與人口老化、社會討論有密切關系;這一些病種恐怕連重疾險的輕癥賠付都沒有觸及,但可以被包裹進健康管理、健康服務、健康體檢;這一些病種的計算保費可能遠遠超過百萬醫(yī)療險保費水平。
即便如此,從患者對需求、風險認知角度,只要市場有顧客,就不應缺少實力、真誠的賣家。比如:百萬醫(yī)療險雖然保費便宜,但客群龐大,有進一步篩分最大支付意愿的客群空間,也普遍認同患者、保險共付機制。
比如:百萬醫(yī)療險的賠付率普遍偏低,把一些病種塞進保障范圍,也有風險加成的剩余空間。重疾險的保費水平相對較高,把一些疾病管理服務塞進保障范圍,折算增加的計算保費也可供潛在投保用戶依據(jù)個性選擇。
假如沒有這些費力的琢磨,就總有一些病種被健康保險遺漏,滾入有風險的用戶、患者全自付的魔力之手。面對全部風險,保險產(chǎn)品理應盡力發(fā)揮風險分攤、削弱的功能,并借支付力整合服務效率,引導就醫(yī)行為。
筆者觀察:當前,我國醫(yī)療行業(yè)內(nèi)部創(chuàng)新很激烈,健康保險行業(yè)內(nèi)部創(chuàng)新也很激烈,且相互需要對方多壓一根稻草支持,在疾病研究、管理這個大命題上,醫(yī)療、保險合力而為,各顯其長,是彼此貢獻的重要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