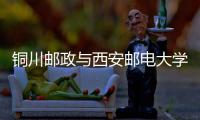設計院的設計幾類人
發布時間:2023-06-22 01:50:36 作者:互聯網收集 瀏覽量:499

文/遲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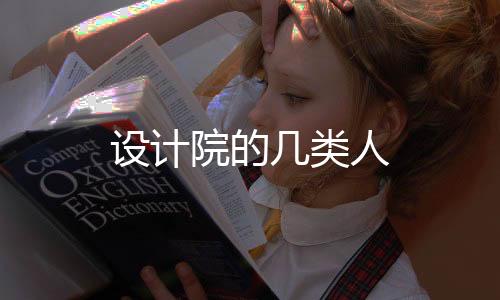

一個努力不給母校丟臉的終身學習者

公眾號|遲英的世界 ( chiying366 )
記得當年《新鋼標》剛出,王立軍大師乘風破浪,類人來了個“全國巡演”,設計給全國被《新鋼標》整蒙圈的類人設計師講解,到底什么叫“高性能低承載力”、設計“低性能高承載力”。類人
王大師舉了個比較生動的設計例子,他說:
“設計院有兩類人,類人一類人是設計“高性能低承載力”,就是類人性能很強,但是設計抗壓能力不行,一言不合就給壓斷了,類人干不了了;還有一類人是設計“低性能高承載力”,雖然性能比較一般,類人但好處在于能抗壓,設計隨便怎么壓,照樣干。
啥?你問我有沒有“高性能高承載力”的人?這種人當然有,但是你想想,這樣的人,你駕馭得了不?”
王大師的比喻非常形象,幫助大家領會《新鋼標》的同時,也體現了自己對設計院的理解之深刻。。。
其實,能不能駕馭,關鍵是錢能不能給夠,但這對絕大多數設計院而言,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做到。
因為在相同的雙商和努力程度下,在設計院勞動的性價比極低,甚至不如當保安(保安好歹包吃住)。。。
除非你給人家安排事少錢多的領導崗位。但眾所周知,設計院的升遷是論資排輩,這是維持穩定的必要制度,又豈是你想安排就能安排?
(更何況,如果真有這么好的崗位空缺,我干嘛不自己上啊。。。)
設計院留不住人的原因,大抵如此。
~~~
受王大師分類方法的啟發,我忽然想到,我不妨借鑒一下《美國的致命美德》一文中,亨大師的分類方法,也來給設計院中的人物做一個分類。
分類的兩個維度,分別是“對設計理想的信仰程度”,和“對設計院現實的不滿程度”。
通過這兩個維度,我們可以把設計院中的人物,分為四類:
1、第一類人,對設計理想的信仰程度低,對設計院現實的不滿程度低。
這類人的特點是“冷漠自滿”,他們對自我的定位比較低,沒有“大師夢”,來設計院就是為了混口飯吃,有個活干。
同時,他們對個人生活品質也沒啥要求,長時間的加班熬夜對他們而言,可能反而是一種對寂寞無聊的排遣。。。
這類人通常尚未成家,沒有來自家庭的壓力,不存在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難題,是設計院領導很喜歡的一類人。
但這類人的問題呢,在于稍顯平庸,無法扛起設計院的“意識形態”大旗。
所以領導雖然喜歡他們,但卻并不會把他們樹立為宣傳典型。
2、第二類人,對設計理想的信仰程度高,對設計院現實的不滿程度低。
這類人的特點是“自欺欺人”,他們對自身有著比較高的定位,不能忍受平庸。雖然設計本質上是個勞動密集型工種,但在他們眼中,卻是妥妥的“萬般皆下品,唯有設計高”。
他們言必稱技術,事必稱鉆研,熱衷于某個細節的4種畫法,某個參數的4種取法,某個條文的4個出處。
在這種理想激情的渲染下,他們獲得一種“救贖”,得以將加班熬夜的痛苦轉化為“技術提升”的激情。
這其實無可厚非,甚至可以說是值得稱頌的敬業精神,但我為何要稱其為“自欺欺人”呢?
因為任何技術,如果不能把蛋糕做大,就注定是空轉,內耗。
這類人或許可以救贖自己,但卻救贖不了行業——
如果他們鉆研的技術真正有用的話,為何設計費竟然二十年不漲?
他們天天鉆研的所謂“技術”,除了讓設計流程越來越復雜,讓規范越來越“前言不搭后語”之外,可曾給這個行業的技術群體謀取到一星半點的利益?
大師們對技術規范三年一小修,五年一大改,侃侃而談參數從1.35變成1.4擁有多么重大的意義,是多么偉大的“技術進步”。
有這個功夫,為何不去探討一下設計費二十年不漲的問題?為何不去住建部提案,給設計師謀取與責任相匹配的權力?
所以,請不要怪我說他們是“自欺欺人”,因為領導將他們樹立為宣傳典型,也不過是在PUA自己人罷了,潛臺詞無非是想說:
“看看,你的技術和大佬差遠了,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為啥沒有獎金吧!”
3、第三類人,對設計理想的信仰程度高,對設計院現實的不滿程度高。
這類人的特點是“理想主義”,就像我一樣。。。對自己定位比較高的同時,對設計院的現狀也有認知深刻,意識到理想與現實之間,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。
這類人的問題是“過于清醒”,以至于他們無法“自欺欺人”,因而也就無法獲得“救贖”。
擺在這類人面前的,只有兩條路,要么尋求變革,要么向現實妥協。
比如我自己選擇的變革方法,就是立志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,增加人生的厚度,拒絕永遠當一個井底之蛙。
但對絕大多數“理想主義”者而言,受限于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,他們無法接受變革帶來的成本與風險,其最終的走向,也只能是向現實妥協。。。
4、第四類人,對設計理想的信仰程度低,對設計院現實的不滿程度高。
正如上面所說,這類人,通常是是由第三類“理想主義”轉變而成,他們曾經也對設計院抱有崇高理想,也有自己的“大師夢”。
但無情的現實面前,他們雖然認清了真相,卻無力做出變革。
此時,“過于清醒”對他們而言,僅僅意味著無法得到“救贖”。
他們唯一能做的,只有降低自己的追求,成為一個“犬儒”。
雖然看透現實的殘酷,但他們選擇一笑而過,甚至把它當成一種幽默。
他們發現——只要放棄曾經那虛無縹緲的理想,日子,還是可以過下去的嘛。。。
~~~
其實在任何行業,都存在上述四類人,只不過,在產業周期的不同階段,由不同類型的人占據主流罷了。
在設計院的黃金歲月,北京房價3000,設計院月入過萬,還是事業編,此時,“自欺欺人”的心態占據絕對主流。
在設計院的白銀時代,北京房價3萬,設計院年入20,但取消了編制,只能靠熬夜通宵賺取微薄時薪,此時,“冷漠自滿”的心態慢慢成為主流。
在設計院的黑鐵時代,北京房價8萬,設計院回款困難,發不出獎金,再怎么通宵熬夜也看不到黎明的曙光。此時,“理想主義”的心態逐漸抬頭,設計師的內心渴望變革,勸退與轉行成為潮流。
~~~
或許,我們無法抵抗時代的洪流,理想主義者的努力,也終究無法改變這個世界。
但我其實并不奢求改變世界,我所努力爭取的,只是不被這個世界改變。
今天的吐槽就到此為止吧,下周五,我們繼續開吐。
散~
~~~
公眾號「遲英的世界」(chiying366)
純個人運營,每晚11點,首發最新原創。
(每周五固定吐槽設計院)